中国抗癌协会
立即下载App《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2023)》——肝胆肿瘤整合护理研究进展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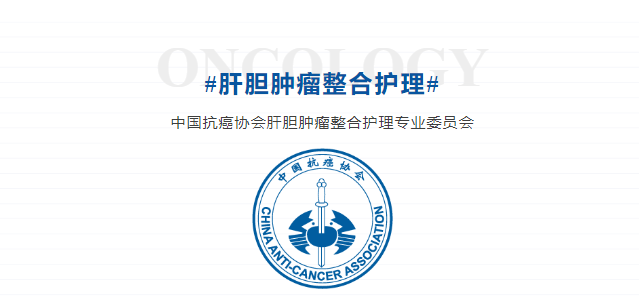

概述
01
肝癌概述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人数仍不断上升。实施精准防控,有效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原发性肝癌(PLC,Primary Liver Cancer)居世界常见恶性肿瘤的第六位,居恶性肿瘤死亡常见原因的第三位。2020年全球肝癌新发病例约有905677例,死亡病例数高达830180例[1]。世界上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亚洲和非洲,其中我国的肝癌患者数量约占全球肝癌患者的一半。目前,肝癌是我国第四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二位恶性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2]。充分了解肝癌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对PLC的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人群肝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分别为17.81/10万和15.29/10万,每年肝癌总发病例数和死亡例数约占全球一半,并具有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别[3]。其中,农村地区人口ASIR和ASMR均高于城市人口,尤其是65岁以下的人口中城乡差异更显著[3]。在地域分布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ASIR和ASMR最高,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3]。同时,研究也显示,我国2019年肝癌的ASIR比1990年下降了58.5%,这可能与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患病率和黄曲霉毒素暴露量的下降有关[4]。
肝癌的发病率与年龄密切相关。我国肝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30岁年龄组的发病率较低,≥30岁年龄组的发病率开始快速升高,80~84岁年龄组的发病率达到高峰。此外,我国肝癌发病的年龄呈逐年增长趋势,农村和城市地区男性平均发病年龄由2000年的56.53岁和59.67岁增长至2014年的61.20岁和62.66岁,农村和城市女性则由60.60岁和65.50岁延迟到66.07岁和69.87岁[5]。
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男性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比女性高2~3倍。在我国,男性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和女性的危险因素暴露率不同有关。研究发现,吸烟和饮酒的男性病毒性肝炎患病率高于女性。另有研究显示,雌激素/雄激素水平与HBV转录和复制的多少有关,这可能与男性HBV感染患者中炎症导致肝癌的发病率高于女性有关[6]。
PLC常见的危险因素包括慢性HBV、HCV感染、酒精性肝病(ALD)、代谢性疾病(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糖尿病(DM)等)。尽管抗病毒药物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乃至根治慢性HBV和HCV感染,但慢性病毒感染仍然是我国肝癌的主要病因。此外,随着肥胖、DM人群的增加,代谢综合征(MetS)、NAFLD的流行更加普遍,将进一步导致肝癌发病率的上升。
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取决于临床分期,其中肝切除术是早期肝癌最常见的根治性治疗方法。但由于肝癌患者常无明显体征或临床表现不典型,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局部进展而无法行根治切除术。近年来,随着各种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的问世,对晚期肝癌的治疗手段实现了突破。在系统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局部治疗能够让部分晚期肝癌患者得到更长的生存期,甚至治愈的机会。目前已建立了多种综合治疗手段,包括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消融治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放射治疗(简称放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7,8]。
02
胆管癌概述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rcinoma,BTC)是一类罕见的、具有高度异质性和侵袭性的肝胆恶性肿瘤。主要包括胆囊癌(Gallbladder Cancers,GBC)和胆管癌(Cholangiocarcinoma,CCA),胆管癌按部位可分为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A)和肝外胆管细胞癌(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ECCA),而ECCA又可分为肝门周围胆管细胞癌(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PCCA)和远端胆管细胞癌(Distal Cholangiocarcinoma,DCCA),约占消化道恶性肿瘤3%[9]。流行病学数据显示,BTC每年约占全球癌症相关死亡人数的2%,BTC全球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以亚洲国家最为常见[10] 。BTC具有早期诊断困难、进展迅速、解剖部位复杂、易复发、预后差等特点,50%的胆道恶性肿瘤患者在确诊时已为进展期,生存期<1年[11]。临床上仅有10%左右的病人就诊时具有手术机会,术后1年内的转移复发率高达67%,5年生存率为5%~15%[12]。未经手术及全身化疗或放疗的晚期胆道肿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短,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未经治疗的晚期胆囊癌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仅在6个月左右[13]。
BTC常见的症状有黄疸、腹痛、恶心、呕吐、上腹部包块等。血清癌胚抗原和糖类抗原19-9在BTC的诊断、疗效和转移复发监测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常与腹部超声相结合,用于高危人群的筛查与随访[14]。超声、磁共振胰胆管成像、CT、MRI及PET/CT是诊断BTC的重要手段,术前的影像学分期常依赖于腹部增强CT或增强MRI。但病理组织学和/或细胞学检查仍是确诊BTC的唯一依据和金标准。对于影像学上高度怀疑BTC且认为不可切除时,需要通过经皮肝穿刺活检、胆道镜活检、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下胆道细胞刷检获得标本进行病理确诊。同时,若可获得足够的组织进行基因检测,可用于指导系统治疗药物的选择,达到精准诊疗的目的。此外,液体活检技术通过对患者体液中的生物分子如循环肿瘤DNA、循环游离DNA进行分子分析,对个体化治疗及预后具有一定价值[15,16]。
手术是目前BTC唯一可能治愈的方法,但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处于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因此系统治疗成为晚期BTC最主要的治疗手段[17]。现阶段,化疗是晚期BTC系统治疗的基础,出现靶向治疗联合化疗、免疫治疗联合化疗、靶免联合治疗等治疗方式,随着精准治疗理念的发展和基因检测技术的进步,更多BTC的治疗靶点被发现,研究者对BTC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为BTC治疗领域带来新的突破,针对BTC的治疗正逐步转向靶向、免疫、化疗的联合治疗模式。化疗与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结合可能为BTC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但目前多数临床研究仍处于早期临床阶段,而未来随着更多免疫联合方案相关研究的开展,将推动更多的新型治疗策略进入临床实践。今后仍需进行更多期临床试验,明确一线治疗方案,筛选出潜在的受益人群,帮助BTC患者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存获益。此外,研究人员仍需加深对BTC发病机制、分子生物学及耐药机制的研究,促进BTC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与护理发展。
03
肝胆肿瘤整合护理概述
近年来随着护理的发展与创新,肝胆肿瘤整合护理进展迅速。中国抗癌协会肝胆肿瘤整合护理专委会注重把握肝胆肿瘤的疾病特点,结合肝胆肿瘤学科护理发展现状,坚持学术与实际并重,搭建理论与应用的桥梁,精准凝练《报告》内容。
中国抗癌协会肝胆肿瘤整合护理专委会关注国内外肝胆肿瘤的前沿研究进展,在肝胆肿瘤国内国际研究新进展板块中系统梳理肝胆肿瘤症状群、延续护理、加速康复外科、安宁疗护方面研究进展,集敏锐性、前瞻性、全局性于一体,为肝胆肿瘤整合护理的优化提供发展思路。在肝胆肿瘤护理国内国际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重要研究平台与研究团队板块中详细阐述目前肝胆肿瘤护理国内国际研究的发展重点和重要贡献力量,体现了护理在肝胆肿瘤诊疗中的价值和科学性。更多的中国研究登上国际舞台,护理疗效数据不断被刷新,不断改变着肝胆肿瘤护理的临床实践。在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现存趋势与不足板块中提出现存趋势是综合护理模式的应用、多学科协同合作、个体化护理、信息化健康教育、康复护理、紧跟临床研究、提升护理质量与安全、创新护理教育、国际化护理方面的研究。虽然护理学科发展迅速,但在学科建设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缺乏系统性的长期研究、护理人员培训水平不一、个体化护理实施不足、康复护理体系不健全、对患者心理健康关注不足、护理研究国际合作程度有限。肝胆肿瘤整合护理坚持在具有理论高度的同时兼顾应用性,以权威、精准的科研成果指导临床工作,探寻实际中的劣势并提出建设性解决意见,提供肝胆肿瘤整合护理新思路。在中国肿瘤护理学科十大前沿进展板块中提出精准护理模式、靶向药物治疗的临床护理、癌性相关疼痛的个性化管理策略、护理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护理团队的跨学科协同、肿瘤护理临床路径的优化、建立护理质量评估体系、应用先进技术的护理实践、恶性肿瘤康复护理、健康教育的全面展开是目前中国肿瘤护理学科的十大前沿进展。《报告》不断探寻肝胆肿瘤整合护理发展新方向,探索学科发展新格局,同时注重多学科的系统参与,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切实发展精准肿瘤医疗与护理。在未来5年发展的战略需求、重点发展方向、发展对策板块中提出综合性研究平台的建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个体化治疗及护理的推进是未来5年发展的战略需求,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早期诊断和预防、症状管理的进一步探索是未来5年重点发展方向,提出跨学科合作机制的建立、科研团队建设、临床研究的推进是未来5年的发展对策。掌握肝胆肿瘤整合护理发展规律,明确学科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进一步优化资源分配,筹划肝胆肿瘤整合护理布局,培育具有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和突破口,对我国创新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肝胆肿瘤整合护理聚焦中国特色,掌握学科发展态势,能够广泛、有效地传播肝胆肿瘤护理相关知识,在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中丰富护理学科内涵,旨在确保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得到全面、协调的护理,以最大化护理效果促进患者长期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深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有效实施。
01
肝胆肿瘤护理国内研究新进展
1.1肝胆肿瘤症状群研究新进展
“症状群”定义为2个或2个以上稳定且相关的症状同时出现,并形成一个群,相对独立于其他群,且群中的症状可能由共同的病理机制引起。由于症状的协同作用,症状群对患者造成的不利影响比单个症状更大,除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外,还可能缩短患者的生存时间[18]。因此,症状群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1)消化道症状群
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影响因素探索中,对采用不同治疗方式的肝癌患者发生恶心呕吐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目前手术切除是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手段,由于手术和麻醉等原因,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PONV)成为肝癌患者术后常见并发症。PONV不仅引起患者感官上的不适,严重时可导致水电解质紊乱、腹内压增加、营养不良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研究指出肝癌患者的PONV发生率为48.30%,女性患者PONV的发生率是男性患者的2.191倍,具有恶心呕吐史或晕动史的患者发生术后恶心呕吐的风险较高,年龄<60岁、手术时间≥120 min、术中阻断肝门静脉≥15 min是PONV的独立危险因素[19]。但因肝癌发病隐匿且发展迅速,确诊时只有不到30%的患者具备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对于无法通过手术根治的患者,经肝动脉介入手术为主的局部介入治疗能够有效控制肿瘤。常见的介入手术方式包括TACE及HAIC。TACE术后患者常会并发化疗相关恶心呕吐(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CINV),CINV根据发生的时间分为急性化疗相关恶心呕吐(Acute 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ACINV)和延迟性化疗相关恶心呕吐(Delayed 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DCINV)。国内学者进一步探索肝癌患者TACE术后发生DCINV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是否焦虑、是否有睡眠障碍、化疗药物致吐风险等级、栓塞剂类型、术后24 h疼痛情况是肝癌患者TACE术后延迟性恶心呕吐的影响因素[20]。CINV的发生不仅会降低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使其产生恐惧心理,降低其治疗依从性。对肝癌患者化疗前综合各种影响因素进行DCINV风险评估,对DCINV风险高的患者进行针对性、预防性干预,减少DCINV风险低的患者止吐药物的使用,成为护理人员新的研究热点。
在评估工具方面,通过对国外常用的两种DCINV风险评估工具,DCINV风险指数(DCINV Risk Index,DCINV-RI)和CINV风险预测工具(CINV Risk Prediction Tool,CINV-RPT)进行比较,评估其在我国人群中的预测价值,研究结果显示DCINV-RI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0.838、0.765、0.603,CINV-RPT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0.863、0.841、0.703,CINV-RPT对TACE术后患者DCINV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高于DCINV-RI,临床建议采用CINV-RPT进行DCINV发生风险的评估和预测[21]。提示护理人员应积极开展评估,利用恰当的工具,早期识别术后恶心呕吐的高危患者,通过精准管理,预防术后恶心、呕吐发生。
在症状管理方面,症状管理理论(Symptom Management Theory,SMT)由症状体验、症状管理策略和管理结局三部分构成,并以单独症状现象为基础,提出假设和验证,并据此制订合理的症状管理策略,从而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22]。基于SMT的护理干预可减轻肝癌患者术后腹胀症状,促进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减轻症状困扰[23]。护理人员可以利用SMT,从患者症状体验出发,在干预中,首先让患者症状自评,通过症状评估,针对患者腹胀的原因进行个体化干预,并对可能引起症状的诱因进行预防性护理,针对患者症状感知进行动态管理,从而达到阻止或缓解症状的目的。前哨症状被定义为能够预测是否存在该症状群及群内其他症状发展情况的一种症状,通过调查症状群内的关键症状,对症状进行管理,能更好地优先满足患者的需求。识别前哨症状有助于更全面、快速、简洁地评估症状群,提高症状管理的有效性。张建凤等[24]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提取症状群后再利用症状首发时间结合Apriori算法来识别症状群内的前哨症状,判定肝癌患者TACE治疗期间发生恶心是其上消化道症状群的前哨症状,前哨症状的确定对提高症状管理效率及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对于前哨症状的研究局限于胃癌、肺癌、白血病等患者,在肝胆肿瘤方面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可针对采用不同手术方式的肝胆肿瘤患者做进一步研究,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护理。症状群的研究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目前对症状群有效干预的研究相对较少,可能的难题是缺少潜在的干预靶点,仍需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
(2)病感症状群
在疼痛症状影响因素探索中,对肝癌进行TACE术后患者疼痛影响因素进行评估,TACE治疗经历、肝癌手术或移植史、DM、慢性肝病史、疼痛史、CRP水平、ECOG评分、术前焦虑与TACE术后疼痛有关[25]。也有研究指出TACE术后疼痛与年龄显著相关,在经历两次及以上药物洗脱微球TACE患者中,年龄大于或等于65岁的患者与疼痛严重程度下降有关[26]。进行肝穿刺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的肝癌患者发生急性中重度腹痛的危险因素包括肿瘤大小、肿瘤数量、RFA腹痛史[27]。国内学者利用年龄、术前疼痛、距肝包膜距离、凝血酶原活动度、碘油剂量、栓塞肿瘤数量6个变量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28],该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99;模型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的AUC分别为0.780和0.788,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之间的一致性良好,构建的肝癌患者TACE术后中重度疼痛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准确度,对预测TACE术后中重度疼痛高风险人群、制订针对性的预防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肝癌术后患者疼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术后疼痛的预测,及早对患者进行针对性干预。但目前有关肝癌术后疼痛影响因素的文章主要集中于患者的生理方面,对于患者的心理及社会层面的研究还比较单薄,而现代医学模式倡导生理、心理、社会全面融合,因此对于今后在肝癌术后疼痛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员可做进一步探索。
在疼痛评估工具方面,临床常用的普适性疼痛评估量表包括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数字评定量表(Numeric Rating Scale,NRS)、词语描述量表(Verbal Descriptor Scale,VDS)和修订版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aces Pain Scale-revised,FPS-R),在肝癌患者TACE术后疼痛评估中,有研究认为FPS-R是应用效果最佳的量表,可作为评估患者TACE术后疼痛强度的首选工具[29]。
在疼痛管理方面,强化疼痛管理,注重对肝癌术后患者疼痛的干预,可从环境干预、疼痛转移、用药护理及放松训练、心理疏导等方面着手,降低其疼痛感并促进其康复。在环境干预及疼痛转移方面,沉浸式虚拟现实(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IVR)技术[30],通过生成多感官、多维度的虚拟环境,患者通过佩戴虚拟现实显示设备和耳机,与外界环境及声音隔离,使整个身心沉浸在动态视景的虚拟环境中,将患者的注意力从疼痛转移到3D环境中去,减少有害神经的刺激,从而有效降低TACE术中患者疼痛程度。在用药护理方面,有学者对肝癌栓塞术后疼痛患者择时给药时间点进行改进,基于人体生物钟及时辰药学理论,结合患者疼痛发生规律,改进给药时间点,将给药时间由09:00、15:00改为15:00、21:00,应用于临床后显著提高栓塞术后患者疼痛控制质量及其对疼痛控制的满意度[31]。多模式镇痛是围术期疼痛管理策略的基础,在应用镇痛药物的基础上,应用阶梯式用药、音乐疗法、意念转移等方式可有效减少患者的用药剂量,降低药物对肝肾的损伤,且可以对术后镇痛药物起到协同作用,延长镇痛时间。提示护理人员应对患者进行全面、有效的疼痛评估,在工作中进一步探索更具临床应用价值的镇痛模式,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提高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
癌因性疲乏(Cancer-related Fatigue,CRF),被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定义为一种扰乱机体正常功能的、痛苦的、持久的、主观的疲惫感,无法通过休息或睡眠缓解,因此严重影响患者康复和生活质量。在CRF症状影响因素的探索中发现,自费患者、病程时间长、对疾病认知程度高、存在辅助化疗以及社会支持度低的肝癌患者CRF得分更低。而以护士为主导,家庭主要照顾者参与的认知和运动训练[32]以及聚焦解决模式联合共情护理[33]都可以明显改善中晚期肝癌患者CRF症状。提示护理人员应该关注CRF发生的高危人群,针对个体化差异提供恰当的护理方式,减轻肝胆肿瘤患者CRF困扰程度。
(3)情绪症状群
肝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病死率高,肝癌患者往往从明确诊断就开始承受着心理、生理的双重压力,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会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降低治疗依从性,影响其生活质量及生存时间。疾病不确定感(Uncertainty in Illness,UI)是指当疾病事件不明确、极度复杂,缺乏相关信息或者无法预测结果时,缺乏对疾病事件判断的能力,研究发现肝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其焦虑程度呈正相关[34],也有研究指出自尊对肝癌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与抑郁症状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乐观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5]。综上所述,通过降低疾病不确定感以及加强患者自尊、乐观的心理干预均有助于减轻焦虑、抑郁症状。
在情绪症状群管理方面,结构式心理教育是指综合运用各种心理干预方法的有效成分,以心理支持为基础,将健康教育、应激处理与应对技巧有机整合的一种综合式心理干预方法。研究指出短期结构式心理教育能有效改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为B/C期的肝癌患者的抑郁情绪,且对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36]。除此之外,综合多种护理教育理论模式[37],使用多平台、多种教育手段对肝癌患者开展包括健康信念教育、心理护理和电话慰问为基础的综合护理教育,同样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生命质量并延长生存期。
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在面对不可预测的临床结局时,会产生习得性无助感。习得性无助感的产生会导致患者怀疑自己不具备治愈疾病的能力,偏执地认为医生、护士,以及各种治疗方法都无法改变病情,国内学者对肝癌介入治疗的患者进行习得性无助感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性别、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介入治疗次数、感知配偶支持水平是其主要影响因素[38]。目前国内对肝胆肿瘤患者习得性无助感的横断面研究甚少,且尚未开展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习得性无助感的纵向研究及干预研究,未来学者们可进一步探索研究。
近年来,对肝癌患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分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提示恐惧疾病进展对肝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有直接预测作用[39],且在复发恐惧应对方式方面研究发现,肝癌根治术后采取回避和屈服方式面对疾病的患者,其恐惧水平更高[40]。目前国内关于肝癌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原始研究增多,但由于评估工具以及纳入人群的不同导致结果出现差异。提示护理人员未来可以利用循证方式进行系统评价,提供科学的危险因素分析,通过对恐惧疾病进展高危因素的评估与不同患者情绪水平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控制负性情绪的发生发展,为临床高质量护理提供借鉴。
心理痛苦为一种多因素的不愉快体验,包括心理的、社会的、灵性的和/或躯体的状态,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从常见的、正常的情绪状态(如脆弱感、悲伤和恐惧)到可能导致缺陷的严重问题(如抑郁、焦虑、恐慌、社交隔离、存在和精神危机等),会影响患者的抗癌效果。研究指出性别、年龄、病程、屈服、回避、面对是肝癌患者首次TACE术后心理痛苦的主要影响因素[41]。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依据,对晚期肝癌患者实施舒缓护理联合心情日记的综合护理干预[42],可降低晚期肝癌患者心理痛苦水平并能改善负性情绪。
1.2 肝胆肿瘤延续护理研究新进展
延续护理是将住院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或家庭,使出院患者能在恢复期得到持续的卫生健康服务,提高患者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症状控制,改善生存质量,从而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因病情变化出现再住院的现象,增加卫生服务成本效益。
多学科协作模式(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MDT)是目前我国医疗机构探索与发展的新方向。多学科协作模式延续护理是将多学科协作和延续护理有效整合,延续护理团队成员中涉及多个具有互补背景和技能的专业人员,提倡团队间合作和交流的动态过程, 最终达到多重保障效应,能更有效、专业和全面地解决患者各方面的需求,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及治疗的依从性[43]。护理人员应注重多学科团队协作交流,加强医护患之间的沟通,共同参与肝胆肿瘤术后患者的出院准备管理,提升其出院指导质量、满足患者出院准备需求。
移动平台可以传输图片、视频、音频等数字信息,患者能够理解并从所传输信息中提取可靠的自我管理措施,从而辅助患者实现各阶段目标,具有方便、快捷、即时的优势,能够满足患者院外延续护理需求。Snyder希望理论模型认为希望是一种目标导向的思维,它包含个人对自己有认知与信念(路径思维)和个人对自己激发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必要动机的认知与信念(动力思维),确定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有助于最终提升患者希望水平。Snyder希望理论与移动平台联合[44],从饮食、用药、锻炼、休息及复查方面确定患者的理想护理状态,构成以Snyder希望理论为中心的肝癌术后出院患者干预策略。即根据理想护理状态建立路径及动力思维,为患者的院外护理提供了方向,使患者的院外康复过程达到最优,实现对患者的延续护理。
纽曼系统护理模式是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以系统观和整体观为线索,对周围环境以及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能够根据压力源和患者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护理,对患者进行调节,使其机体保持动态平衡。与微信平台干预相结合,可以将护理延伸到院外给予患者专业的建议及指导,提高自我管理能力[45]。微信平台干预有利于拉近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满足患者需求,对患者进行循序、有效的指导,提高患者对肝癌的认识程度,缓解患者焦虑情绪,提高服药依从性。晚期肝癌患者院外照护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社区照护、居家护理及养老院照护,为符合我国医养结合服务的要求,为患者提供综合性、连续性及无缝隙的护理照护,整合社区、医院、居家护理和养老院多方资源,建立“医养结合-四元联动”整合照护模型[46],为患者提供可靠的院外照护。医养结合-四元联动整合照护关注各医疗机构及家庭之间的联动,依托电子档案及互联网+技术,完善医院、社区、家庭及养老院间患者信息的共享,而医患沟通平台的构建,也意味着新型网络沟通方式将减少医患沟通障碍,在现代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肝胆肿瘤加速康复外科研究新进展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是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 通过外科、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协作,对涉及围术期处理的临床路径予以优化,通过缓解患者围术期各种应激反应,达到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及促进康复的目的[47,48]。
2019年11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在2019-202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这是ERAS首次作为主角,出现在国家最高卫生行政机构的文件中。2021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和麻醉学分会再次共同发表了《中国加速康复外科临床实践指南(2021)》[49],这也是加速康复外科在中国推广应用道路上里程碑式的进展。为进一步推进加速康复外科诊疗理念和诊疗模式在外科领域的应用,国家卫生健康委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和有关医疗机构典型做法,于2023年4月发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加速康复外科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函〔2023〕107号)》。近年来,随着精准理念及微创技术的推广普及,ERAS理念及路径在肝胆外科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逐渐建立相关的专家共识及临床指南,临床实践也表明了肝胆外科围术期实施ERAS是安全有效的。目前治疗肝胆疾病,外科手术治疗依然是首选方式,但肝胆外科手术操作复杂,具有技术要求高、标准术式少、术式变化大等临床特点,围术期应激反应及并发症的发生率往往差异很大。因此,肝胆外科开展ERAS较其他专科更具复杂性,如何提高肝胆肿瘤手术患者术后康复进程一直是ERAS关注的重点内容。
国内学者以整体护理理论为核心指导思想,以OPT(结局-现存问题-检测)为结构框架,以最新临床专家共识为内容依据,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ERAS肝癌患者围术期护理方案[50],最终构建了包括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和40项三级指标的ERAS肝癌患者围术期护理方案,条目内容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内容效度指数为0.92,表明其护理方案干预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护士实施临床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标准,可使护士在临床实践活动中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更加关注围术期的护理难点和核心问题,提高护理质量和工作效率。国内学者研究国内外关于肝癌患者TACE加速康复管理的证据,共总结出TACE加速康复管理的最佳证据有27条,包括“术前健康宣教与管理”、“术后并发症的管理”、“术后早期活动时间及安全性、必要性”3个方面内容,为相关科室临床护理实践提供了循证依据。
预康复(Prehabilitation)是近年来基于ERAS理念提出的一种在患者手术等待期间进行术前优化的主动过程,是ERAS措施实施的细节化及术前准备的规范化,有利于让患者以更好的状态应对手术所带来的创伤[51]。《中国加速康复外科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将预康复的实施作为强烈推荐,其主要内容包括:术前贫血的纠正、预防性镇痛、术前衰弱评估、术前锻炼、术前认知功能评估、术前炎症控制、术前心理干预等。有学者总结了基于ERAS理念的预康复在腹部大手术中的研究进展,从预康复的概念、目的、实施、内容及应用现状五个方面进行综述,并提出对预康复研究的建议,以期为临床开展预康复实践提供参考。目前国内倡导的主要是三联预康复策略,即手术等待期中高强度的有氧及力量锻炼、蛋白补充为主的营养支持、心理支持消除焦虑。有研究对120例行腹腔镜肝切除术的肝癌患者实施三联预康复策略,干预时间约2~4周,结果表明,观察组术前1天、术后4周的六分钟步行距离(6-min walking test,6MWT)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运动训练可提高患者身体机能状态;观察组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HAD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提示心理干预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观察组术后4周ALB、PA、TRF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 ,提示术前营养支持改善了患者的营养状况[52]。
ERAS全程胃肠道管理是通过加速康复的一系列措施,促进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研究指出在ERAS的标准路径管理下,全程胃肠道管理是安全有效的且对减轻患者口渴饥饿等不适症状、促进胃肠功能早期恢复、改善营养状况、保护肝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早期康复具有重要意义[53]。术中低体温预防是ERAS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应用循证实践的方法制定了基于最佳证据的肝癌ERAS术中保温技术方案[54],为临床护理人员提供低体温预防规范。
在ERAS理念指导下,对肝胆胰手术术后腹腔引流管实施精准管理可以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达到加速康复的目的。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仍较少,如何实现肝胆胰手术腹腔引流管的精准管理尚缺乏共识。为了更精确实施“不常规放置引流管、尽早拔除引流管”这一ERAS理念在我国肝胆胰外科中的发展,实现术后引流管的精准管理,国内有学者系统回顾了关于肝胆胰外科手术腹腔引流管管理的最新研究,对引流管的置管、拔管指征及引流管留置时间与术后并发症的关系进行了归纳总结,对实现术后引流管的精准护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55]。
国内学者对传统的出院准备管理方案进行优化,研究构建的ERAS肝癌患者出院准备管理方案[56]可提高肝癌术后患者的出院指导质量,改善出院准备度,能帮助肝癌患者更顺利地实现医院向家庭和社会的过渡,居家康复效果更加理想,再入院率更低,在促进ERAS肝癌术后患者康复方面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可满足患者多样化的出院宣教需求及居家护理技能需求。
为了规范肝胆肿瘤外科手术的加速康复护理行为,提高ERAS质量,有学者基于零缺陷管理理论构建肝胆外科加速康复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ERAS实施效果提供依据,填补了专门针对加速康复外科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空缺。该研究以零缺陷管理为理论指导,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涵盖3项一级指标(保证体系、运营管理、控制体系)、8项二级指标、39项三级指标的肝胆外科加速康复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指标重要性评分>4分,变异系数为0~0.166,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合理,有较好的可信度,可作为肝胆外科加速康复质量评价工具[57]。
国内对ERAS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循证护理实践, 要求护理研究人员首先提高对循证护理及证据应用的认识。其次ERAS理念要求医护一体, 充分落实相关措施,培训改进实施流程,确保基于最佳证据的护理行为落到实处。ERAS运用科学的方法不断改进临床护理实践,使护理与医疗发展相匹配,推动了护理学科的发展,但ERAS仍需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优化、改进, 真正做到让患者受益。
1.4 肝胆肿瘤安宁疗护研究新进展
安宁疗护是指由卫生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提供的生命末期照护,包括医疗、心理和精神支持,通过控制疼痛和其他症状,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临终患者获得平和、安慰和尊严[58]。目前,安宁疗护的研究内涵包括保持患者生理舒适、减少痛苦(环境、睡眠、疼痛、疲劳、清洁),维护患者尊严(生命意义感、治疗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同伴支持、经济支持、家人陪伴),帮助患者平静离世(宗教需求、预立医疗照护、死亡恐惧)等。
常用的关于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需求的评估工具主要有:姑息照护评价工具(Palliative Care Assessment Tool,PACA)[59],癌症病人姑息照护的需求评估表(Problems and Needs in Palliative Care,PNPC)[60],安宁疗护需求评估(Patient Needs Assessment in Palliative Care,PNAP)[61],癌症病人安宁疗护需求问卷[62],姑息照护结局量表(Palliative Care Outcome Scale,POS)[63]等。
目前,国内对如何为晚期肝癌术后患者实行系统科学的安宁疗护尚处于探索阶段。肝癌晚期患者由于肿瘤体积不断增大常常伴有疼痛、纳差、营养不良,肝硬化患者会出现腹水、腹胀、双下肢水肿。肿瘤的压迫则会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引发全身皮肤瘙痒。更严重的是,由于肝硬化的加重,会导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严重影响晚期肝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早期识别晚期肝癌患者安宁疗护需求十分必要。
有国内学者[64]通过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了解晚期肝癌介入术后患者的安宁疗护需求,最终凝练出4个主题:缓解生理症状,包括缓解恶心、呕吐的不适症状和缓解疼痛的症状;心理需求,包括得到情感支持的需求、满足内心愿望的需求和得到亲属照顾的需求;健康管理相关知识的需求,包括了解肝癌相关知识的需求和掌握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管护理的需求;降低经济负担的需求。崔雪等[65]对晚期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需求现状调查显示,照顾者需求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疾病知识(4.51±0.41)分,医护相关行为(4.20±0.42)分,对患者症状控制(3.79±0.73)分,临终关怀知识(3.67±0.86)分,对患者心理支持(3.48±0.96)分,家属自身健康(3.25±0.82)分,丧葬支持(2.84±1.29)分。沙小琴等[66]探讨临终关怀干预在肝癌晚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的总蛋白、清蛋白、血红蛋白水平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疼痛、焦虑、抑郁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周小丰等[67]探讨基于生命意义的死亡教育在肝癌患者晚期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结果显示观察组紧张、愤怒、压抑、自尊感、慌乱情绪评分,死亡态度与生活质量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综上可知,晚期肝癌患者及家属对症状控制、情感支持、临终关怀等方面存在较高需求,而开展针对性的安宁疗护干预,对帮助患者管理不适症状,满足患者及家属的心理需求,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有积极意义。
02
肝胆肿瘤护理国际研究新进展
2.1 肝胆肿瘤症状群研究新进展
2020年,全球估计有905700人被诊断患有肝癌,830200人死于肝癌,预计在2020年至2040年间,每年肝癌新发病例数将增加55.0%,2040年可能有140万人被确诊,据预测,2040年可能有130万人死于肝癌(比2020年增加56.4%)[68]。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未来20年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将会上升,预计病例的增加可能会增加对肝癌患者管理护理资源的需求,护理工作面临新挑战。
(1)消化道症状群
栓塞后综合征(Postembolization Syndrome,PES)是TACE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腹痛、恶心和呕吐。有研究对30名肝癌患者实施音乐疗法,参与者在参与期都有轻微的腹痛、恶心和呕吐,采用转换设计,比较患者从实验期到另一个对照期的腹痛、恶心和呕吐的变化,结果显示在TACE后的第0、1、2天,音乐治疗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低于基线,但两组恶心、呕吐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音乐疗法可有助于控制肝癌TACE术后疼痛,但在改善术后恶心、呕吐方面效果有待进一步探究[69]。提示音乐疗法可作为护理人员护理肝癌患者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之一。
舒适护理理论涵盖了身体、心理、社会文化和环境领域的四种舒适需求。TACE术后PES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并影响其整体的生活质量,一些需要反复TACE干预的患者也可能因PES和症状干扰而拒绝持续治疗,护理人员感知到的最常见的PES体征和症状干扰是发热和情绪变化,只有在护理人员同时察觉到PES体征和症状困扰时才提供社会文化和环境护理[70],然而接受TACE的患者很少表现出他们的症状和体征,因害怕分散医护人员对整体疾病诊治和护理的注意力,患者会尽量避免报告不适症状,护士很难发现患者住院期间的不适,因症状管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身体舒适度的一个重要举措。提示在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应积极鼓励患者自行报告因PES和症状困扰而经历的不适感,从而及时为患者提供舒适护理,提高护理满意度,改善生活质量。
(2)病感症状群
了解晚期肝癌患者所经历的普遍症状和症状困扰,对于设计全面且适合患者的症状管理策略,优化临终关怀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有学者对18例肝癌晚期患者临终前存在的症状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缺乏活力和疼痛是最常见和最令人痛苦的症状[71],提示护理人员可通过对痛苦症状的讨论,为患者提供基于个体需求的全面整体护理。
在评估工具方面,MD Anderson症状量表-胃肠道模块(M.D.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gastrointestinal Cancer,MDASI-GI)、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核心30项生活质量问卷(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Core Questionnaire,EORTC QLQ-C30)、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肝癌18项问卷(Quality of Lif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EORTC QLQ-HCC18)、癌症治疗功能评估-肝胆功能评估(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hepatobiliary,FACT-Hep)可用于肝癌的疼痛评估研究。
研究指出肝切除术后患者早期进行标准化体育活动[72],可减轻肝癌术后疼痛程度并减少镇痛剂的使用和副作用,改善睡眠质量,缓解疲乏,在减少护理工作量的同时也能减轻患者痛苦,实现快速康复。
(3)情绪症状群
患者在确诊为肝癌后,承受着经济和痛苦的双重压力,容易产生焦虑、对生活绝望、对治疗失去信心的情绪,有的患者因体检或无意中发现肝癌而表现出否认、恐惧、悲观或拒绝治疗。早期心理护理干预能加强患者与家属以及与医务人员的沟通,根据患者的个性特点、心理状态、文化水平提供心理疏导,介绍目前肝癌治疗的手段和方法,说明治疗的目的、优势、适应证、治疗效果,密切关注患者干预后的心理状态,有研究指出护士主导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肝癌患者的焦虑、抑郁[73]。但是目前针对肝癌患者心理教育计划的具体内容和策略的尚未达成共识,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关注。
2.2 肝胆肿瘤延续护理研究新进展
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仅依靠药物来治疗晚期肝癌患者已成为历史,全面的护理干预则变得非常重要。
国际上,在肝胆肿瘤护理工作中充分重视护理人员的协调工作[74]。设置专职护士协调员,即为患者提供信息与咨询,护理人员可通过促进患者与初级保健服务之间的沟通,帮助患者克服障碍,高效率完成初次或再次就诊工作。有研究指出在调查的一年时间里,专职护士协调员能够有效避免175次门诊就诊,其中113次是通过护士独立执行和启动 MDT会议实现的,10次是通过护士主导健康教育实现的,52次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临床活动(如在社区进行数据检索和上传)实现的。在患者诊疗过程中,专职护士协调员的角色也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每年节省的最低成本为85750澳元[75]。
延续护理干预侧重于全心全意和个性化的护理,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防御机制。患者住院期间由护士主导的教育可帮助他们为出院做好准备,如告知潜在并发症、协助药物管理、支持护理规划和协调,促进向社区护理过渡[76]。也提示护理人员在护理路径的各个阶段,根据患者的文化、认知和情感需求量身定制教育非常重要。
2.3 肝胆肿瘤加速康复外科研究新进展
ERAS护理计划是一个源于循证医学的外科概念,旨在通过优化围手术期临床管理路径减少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应激和术后并发症,以实现更快的术后康复。
护士作为与围手术期患者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员,在ERAS路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Meta分析提示ERAS护理计划能够降低肝切除术患者手术部位发生伤口感染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促进术后恢复[77]。
有研究进一步探索肝切除术后患者ERAS方案依从性与术后预后的关系[78],研究共纳入436例患者,根据患者ERAS方案依从性分为两组,结果显示较高的ERAS方案依从性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低,且会缩短术后住院时间。此外,多学科方法与辅助化疗是在肝胆肿瘤治疗中取得最佳疗效的关键因素,然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可能会延长手术与化疗之间的间隔时间,从而对肿瘤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共纳入44名接受辅助化疗的肝癌患者,结果得出ERAS方案依从性≥67%的年轻患者(年龄小于65岁)无论是否有严重的并发症,手术与化疗之间的间隔时间都会显著缩短(缩短10天),达到改善预后的临床效果[79]。提示护理人员应该通过提高患者ERAS方案依从性,进一步提高肝胆肿瘤患者生活质量。
2.4 肝胆肿瘤安宁疗护研究新进展
临终关怀服务能够显著改善对各种慢性病和危重症患者的护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目前已被视为晚期疾病患者标准护理的一部分。
临终关怀偏好可以定义为患者希望从自身的临终护理中得到什么。国际上关于临终关怀偏好的内容主要涉及护理地点、死亡地点和临终护理目标偏好等方面。由于癌症患者的临终关怀偏好存在差异,了解其临终关怀偏好可以让医护人员更清楚患者的担忧[80]。提示护理人员可以根据肝胆肿瘤患者的临终关怀偏好对其进行合理转诊,调动家庭、医院及社会等多方力量,建立全方面的支持网络,提供包括患者和照顾者在内的整体照护,为患者提供满意的个性化临终服务,改善临终关怀结果,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分配。
Avila等人[81]利用美国国家医保系统样本人群来评估临终关怀对肝癌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晚期患者(与没有接受安宁疗护者相比)有较长的中位生存期(76.5天VS 66天),较低的住院死亡率(1.1% VS 25.5%)和较低的每日费用中位数(951美元VS 1004美元)。然而,在65岁及以上被诊断患有肝癌(预后不良)的人群中,只有25%的人员较早接受了临终关怀,大多数人只在生命的最后几周才关注临终关怀。
Fukui等人[82]调查有医疗保险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终关怀对资源利用和死亡率的影响。通过使用流行病学和营养学数据库进行横断面研究,研究共纳入3385名肝癌患者,结果显示年龄较大、肝硬化失代偿期和肿瘤晚期与临终关怀时间缩短有关,而亚洲/太平洋岛民种族和放射外科手术史与临终关怀时间延长有关。与接受临终关怀者相比,从未接受临终关怀者的住院费用更高,且在病程早期接受临终关怀并放弃积极的治疗并不会缩短患者的死亡时间,反而可能会让患者在确诊后活得更久,即肝癌患者实施临终关怀可提高生存率和资源利用率。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临床和人口统计学因素阻碍临终关怀的实施,提示护理研究人员要充分研究探索对肝胆肿瘤患者实施临终关怀的障碍因素并采用积极处理方式,如护理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背景的患者时采用跨学科团队方法(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医疗翻译者等),为肝胆肿瘤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临终关怀护理服务。
近年来,临终关怀也更注重对晚期肿瘤患者临终时家庭照护者的研究,通过收集访谈数据,采用常规内容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确定了5个核心类别和9个子类别,从终末期诊断到生命终结,肝癌患者家庭照护者感到没有准备、不确定、需要信息帮助[83]。提示护理人员可通过引导家庭照顾者关注知识学习及疾病症状的表现和解释说明,帮助家庭照顾者了解症状评估和管理,并帮助患者及时转诊进行姑息治疗。研究发现,死亡患者的5.7%~11.3%的核心家庭成员伴随有心理障碍,家庭成员的不良心理状态也会对患者造成负面影响[84],临终关怀护理不仅可以缓解晚期肝癌患者的疼痛程度,提升其临终前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还可改善核心家庭成员的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85]。临终关怀从患者延伸到患者家庭,更体现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肝胆肿瘤护理国内国际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重要研究平台与研究团队
01
肝胆肿瘤护理国内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目名称:肝胆肿瘤个体化护理与治疗研究
主要内容:该项目旨在通过整合基础研究、临床试验和护理实践,推动肝胆肿瘤护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研究和应用。
(2)项目名称:肝胆肿瘤新辅助治疗的模式及方案选择
主要内容:从肝胆肿瘤新辅助治疗的病人筛选、治疗模式与方案选择、不良反应监测与防治、手术时机及术后治疗等方面进行归纳与探讨,为肝胆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提供诊治思路。
(3)项目名称:肝胆肿瘤护理新技术与新方法研究
主要内容:支持在护理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提高肝胆肿瘤护理的技术水平。
(4)项目名称:肝胆肿瘤患者的症状管理、康复和随访体系研究
主要内容:通过饮食调整、心理辅导、康复训练等方式,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实施有效的随访策略,及时发现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提高患者生存率。加强患者教育和自我管理,使患者更好地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掌握正确的康复方法和注意事项,提高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测的能力。
1.2“十三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项目名称:肝胆肿瘤新型药物研发
主要内容:该专项旨在加强肝胆肿瘤药物的研发,包括药物的创新与应用,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
02
肝胆肿瘤护理国际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
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肝癌护理计划
主要内容:WHO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肝癌护理计划,致力于改善肝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该计划包括护理标准的制定、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多个方面。
2.2 International Liver Cancer Association(ILCA)临床研究项目
主要内容:ILCA积极推动国际上肝胆肿瘤护理的临床研究,关注不同地区和人群的护理差异,为全球范围内的最佳护理实践提供支持。
03
肝胆肿瘤护理国内国际重要研究平台
3.1 国内重要研究平台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肝胆肿瘤护理研究中心
主要内容:该研究中心集结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开展肝胆肿瘤护理的前沿研究,包括护理策略、药物研发等方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肝胆外科与护理团队
主要内容:该团队在肝胆外科和护理领域取得显著成果,不仅在临床治疗方面有突出表现,同时也注重护理和康复工作。
(3)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肝癌护理团队
主要内容:该团队专注于肝癌患者的护理和康复,通过开展临床研究和护理实践提高肝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4)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医疗护理团队
主要内容:该团队为推动肝胆外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团队不仅在技术层面卓越,还注重对患者的护理,致力于提供全面而温暖的医疗服务,为患者的康复和健康保驾护航。
(5)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肝胆胰外科与护理团队
主要内容:全面推广加速康复理念,有效改善患者结局,持续提升患者满意度。强化大器官移植护理技术体系创新,实现大器官移植临床护理服务能力全国顶级。成为大器官移植专科护理技术人才培育与输出地。基于临床实践,发挥临床资源优势,开展高水平护理研究。
(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脏外科
主要内容:该团队成功绘制出基于中国人群的肝内胆管癌的“基因图谱”,揭示其基因变异特征。这也是国内首次针对肝内胆管癌的大人群、大规模基因组学研究,将为国人肝内胆管癌患者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精准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基础数据。
(7)浙江省肿瘤医院 介入及肝胆内科与护理团队
主要内容:该团队专注于肝胆肿瘤的系统治疗,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及新材料研发,一方面通过多组学及肠道菌群筛选胆道肿瘤免疫治疗优势人群,构建筛选模型;另一方面,开展多项临床研究探索肝胆肿瘤新的治疗模式,以求为肝胆肿瘤患者制定个体化、精准化的系统治疗方案。护理团队总结肝胆介入20余项专科护理常规和流程,开展肝癌TACE、HAIC等介入专科护理系列研究,发表多项论文,编写专著与共识,申请多项专利。同时申办国家级和省级继续教育项目,在肿瘤介入护理规范化推广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2 国际重要研究平台
(1)Mayo Clinic Liver Cancer Program(美国梅奥诊所肝癌项目)
主要内容:作为综合性的肝癌研究平台,该项目集结了梅奥诊所的专业力量,涵盖了肝癌护理的多个方面,包括临床治疗、基础研究等。
(2)European Network for the Study of Cholangiocarcinoma (ENS-CCA)
主要内容:该网络致力于研究胆管癌(胆管细胞癌),促进欧洲范围内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推动胆管癌护理的国际标准化。
(3)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项目名称:Liver Cancer Consortium
主要内容:该项目旨在促进国际上对肝癌的多学科研究,包括护理、治疗、预防等方面的合作。
(4)欧洲癌症研究组织(EORTC)
项目名称:Cholangiocarcinoma Platform
主要内容:该平台致力于研究胆管癌(胆管细胞癌)的治疗和护理策略,为欧洲范围内的研究提供支持。
(5)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主要内容:安德森癌症中心在癌症治疗和科研领域中排名全美第一,并且连续7年在美国癌症研究医院评比中排名第一。该中心为癌症患者提供的治疗包括靶向疗法、手术、化疗、放疗和质子疗法、免疫疗法以及多种疗法的联合治疗。跨学科的专家团队通过密切合作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
(6)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Dana-Farber Cancer Center)
主要内容: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癌症专科附属医院、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癌症患者提供专业、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时通过前沿研究提高对癌症及相关疾病的认识、诊断、治疗及预防等。
(7)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
项目名称:LEAP-002和SHR-1210-Ⅲ-310(NCT03764293)晚期一线HCCⅢ期临床实验
主要内容:该项目旨在研究对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CC患者全身治疗的方式和时机。该平台致力于推动欧洲范围内与肝胆肿瘤的治疗与护理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为肝胆肿瘤相关的临床研究提供支持。
(8)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
项目名称:HYMALAYA研究
主要内容:该项目是ASCO胃肠肿瘤研讨会发布的首个获得OS阳性结果的双免疫联合一线治疗不可切除的HCCⅢ期临床试验。该平台旨在促进将癌症相关研究成果转化到临床应用,不断改善癌症诊疗和护理质量。
在这些重大计划、研究项目和研究平台的推动下,肝胆肿瘤护理领域正逐步迈向更为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和关怀。各国研究团队的合作也为该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领域研究不断深入,未来将有更多的计划和项目涌现,为肝胆肿瘤护理带来更多创新和突破。
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现存趋势与不足
01
研究趋势
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呈现出多个明显的趋势。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我国在临床实践和科研领域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对患者护理质量和效果不断提升的关切。以下将详细阐述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的现存趋势。
1.1 综合护理模式的兴起
近年来,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注重从传统的疾病治疗向综合护理模式的转变。这一趋势在肝胆肿瘤护理实践中得以显现,体现为将多专业、全过程的护理模式引入患者的护理计划中。
综合护理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从多个层面照护患者,全面关注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包括症状管理、心理护理、社会干预以及中医护理等多项护理措施的综合应用[86],为肝胆肿瘤患者提供更全面、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满足患者多元化的护理需求,从而促进其身心健康,提高整体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从传统的疾病治疗迈向综合护理模式的转变,体现了对患者全面关怀的追求和对护理理念的不断创新。这一变革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更为肝胆肿瘤患者带来更为人性化和个体化的护理服务,使其保持乐观、理性、正确的疾病认知。在未来,随着综合护理理念的不断深入,肝胆肿瘤护理学科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2 多学科协同合作
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的另一显著趋势是多学科协同合作的护理模式。多学科协同合作护理模式作为新型的护理模式,依据患者生理、心理等实际需求,组建多学科护理小组,纳入专科医生、护理人员、营养师、康复训练师、心理咨询师及其他医护人员等,确保肝胆肿瘤患者在围手术期、化疗期、康复期等各个阶段均能接受多元化专业的护理服务,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87]。专科医生负责对肝胆肿瘤患者临床评估、诊断及治疗。营养师负责全疗程的营养管理,讲解维持良好营养状态对提高免疫功能,促进切口愈合的重要性,提供个体化营养支持方案,动态监测人体营养指标。康复训练师负责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督导患者实施康复锻炼计划,加速患者康复。心理咨询师负责心理评估及个性化心理干预,有效疏导负面情绪,改善心理状态。护理人员负责全程病情追踪和反馈、健康教育及临床护理,协调团队合作,优化医护资源,促进多学科共同发展,深化护理质量内涵[88]。
多项研究均证实多学科团队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肝胆肿瘤患者术后疼痛程度,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快速康复。此外还可以调节肝胆肿瘤患者身心状态,减轻负面情绪,提高社会支持程度,护理价值较高[43,89]。多学科协同合作的护理模式有助于充分发挥各专业的优势,关注患者多元化需求,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护理服务,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满意度。
1.3 推行个体化护理
个体化护理是近年来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护理的发展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更着眼于患者个体差异,增强自我照护能力,强调个体化护理的重要性。肝胆肿瘤患者因癌症类型、病程阶段、身体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个体化护理干预通过对患者机体情况、疼痛耐受程度、心理、生理等情况进行观察评估,采取有计划、靶向性护理干预对策,提供全人、全程的个体化护理服务,很好地弥补了常规护理的缺陷,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90]。
研究显示个体化护理管理从生理、心理、精神、社会等多方面进行干预,可有效调动肝胆肿瘤患者的积极性,使其提高对肝胆肿瘤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调节不良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早期恢复,从而保证临床治疗的有效性,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91,92]。
1.4 信息化健康教育
在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中,越来越强调对患者进行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健康教育。信息化健康教育护理干预通过应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手段,以图片、展板、视频、科普等素质化教育宣教途径,将肝胆肿瘤相关抽象、难懂的专业理论知识加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呈现,更好地调动患者对于肝胆肿瘤知识参与的积极性与兴趣[93]。
信息化健康教育不仅停留在传递知识的层面,更强调培养肝胆肿瘤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向患者提供关于疾病、治疗、饮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知识,鼓励患者主动参与健康管理,增强健康意识,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94,95]。此外,信息化健康教育,能够快速、有效地整合、传递健康知识,从而使患者更容易了解到肝胆肿瘤的风险因素、预防措施等方面的内容,从而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疾病,有助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有益于康复和预防的决策。
有研究表明护理人员还可借助互联网信息交流技术,对患者进行远程延续性健康行为宣教与指导,促使患者养成较为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96]。综上所述,对肝胆肿瘤患者采取基于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护理措施,可有效改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水平和日常生活质量水平。
1.5 更加关注康复护理
随着对患者整体生存质量关注的增加,康复护理逐渐成为肝胆肿瘤护理研究的热点之一。传统护理主要侧重于疾病的治疗和症状的缓解,而康复护理则更加注重患者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患者在面临肝胆肿瘤等严重疾病时,不仅期望获得有效的治疗,更渴望通过康复护理帮助其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促进身体和心理的康复,使其在康复过程中能够全面而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
近年来,肝胆肿瘤康复护理的研究关注点集中于快速康复护理,旨在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治疗后的生活。快速康复理念是指以患者为中心,将循证理念和快速康复理念相结合,制定切实符合患者护理需求的康复计划。多项研究表明基于快速康复理念的个体化护理干预可缓解肝胆肿瘤患者的疲乏程度、减轻疼痛感知程度、促进患者快速康复,提高生活质量[56,92]。
随着康复护理在肝胆肿瘤护理中的不断深入研究,关注患者整体生存质量的护理模式逐渐完善。这种模式不仅关乎患者的身体康复,更注重心理、社会和生活的全面康复,为患者提供多方面多维度贴心的医护服务。这标志着肝胆肿瘤护理的发展不仅是医学治疗的进步,更是对患者全方位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回应。
1.6 紧跟临床研究
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逐渐加强对临床研究的关注,通过深入的临床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肝胆肿瘤的发病机制、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为护理实践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近年来临床研究致力于优化肝胆肿瘤患者的护理干预方案,包括手术前后的护理措施、化疗和放疗的护理支持、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等[97,98]。通过系统性的研究,不断改进护理干预方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此外临床研究关注护理质量的评价与提升,通过跟踪患者的护理过程和结果,评估护理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99]。同时,积极探索提升护理质量的策略,包括培训护理人员的技能、制定护理指南和流程、循证护理的应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等。临床研究还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在护理中积极开展心理支持和康复护理,帮助患者应对治疗过程中的身体和心理困扰,提高生活质量和自护能力[42]。
将科研成果应用到护理工作中也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通过将最新的科学发现融入护理实践,护理人员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治疗护理方向,有效地应对患者可能面临的问题。这种科研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有助于提高护理水平,为患者提供更为安全、高效的护理服务。
总体而言,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对临床研究的关注,为护理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护理工作者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关注患者的个体差异,为每位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护理,推动整个护理领域的进步。
1.7 护理质量与安全的提升
在当今医学领域,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正聚焦于如何提升护理质量与安全。近年来,针对提升肝胆肿瘤护理质量的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临床实践方面。一些研究致力于优化肝胆肿瘤患者的个性化护理方案[100,101],通过分析大量患者的病例数据和治疗效果,研究人员努力找到最有效的护理策略,以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和生存质量。此外,一些研究关注于疼痛管理[102,103]、并发症预防[104,105]等方面的具体实践,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安全水平的提升也是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关注的核心。医疗机构采用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实施标准化的手术、治疗以及护理流程,以减少操作失误和患者风险。另外,强调团队协作和跨学科合作的模式也逐渐得到应用,确保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护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同时治疗方案本身也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如何有效预防和应对这些潜在风险,确保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安全,也是护理学科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护理实践中的安全隐患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出科学的安全管理模式,可以为提升整体护理安全水平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加强护理质量与安全的提升是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的核心热点。通过深入优化肝胆肿瘤患者的个性化护理方案以及实施标准化的手术、治疗以及护理流程,肝胆肿瘤护理将迎来更为全面、科学的发展,为患者提供更为安全、有效的护理服务。
1.8 护理教育的创新
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也在护理教育方面进行创新。首先,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在教育中注重培养护理人员的多学科综合思维能力。肝胆肿瘤的治疗涉及外科手术、内科治疗、影像学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护理人员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因此,创新的护理教育模式不仅注重传授基础的护理知识,更强调培养学生在多学科多领域协同工作的能力、临床决策能力和全局观念,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医学环境。
其次,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是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在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临床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护理环境中接触到肝胆肿瘤患者,亲身体验和应用所学知识。通过实践,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护理工作的复杂性,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在护理教育方面的创新是为了培养更全面、更专业的护理人才,以更好地满足现代医学的需求和社会对护理服务的期望。
1.9 交流合作国际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也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首先,与国际上的护理学科进行交流合作,是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追求卓越的必由之路。通过参与国际性学术会议、研讨会,我国护理专业人员可以与世界领先的学者、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肝胆肿瘤护理领域的前沿问题。这有助于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提升我国护理学科的学术水平。
其次,分享经验和学习先进技术是这一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的医疗挑战各异,通过与国际上的同行进行经验分享,我国护理学科可以借鉴其他地区在肝胆肿瘤护理方面的成功实践,优化我国的护理模式。同时,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如新型医疗设备、护理方法等,有助于提高我国肝胆肿瘤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应对复杂病例的能力。
总的来说,随着国际化的推进,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与国际接轨将为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一国际合作势必推动我国护理学科走向更高层次,为临床实践和患者服务提供更为全面和优质的支持。
总体而言,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正朝着综合护理模式、多学科协同合作、个体化护理、信息化健康教育以及深入临床研究等多个方向发展。这些趋势的出现使得肝胆肿瘤护理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科技的不断发展,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也需要不断创新和进步,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多层次需求。
02
存在不足
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以下将进行详细探讨。
2.1 缺乏系统性的长期研究
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中存在着对患者长期跟踪和系统性研究的不足,大多数研究更侧重于特定治疗阶段或特定护理干预的效果,而对患者的长期康复和生活质量缺乏全面研究,影响了个体化护理的实施。
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进行护理学科研究方法学的培训,提高研究人员对于长期跟踪和系统性研究认识方法的掌握。其次,建立健全患者信息系统,实现对患者全程信息追踪,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同时,鼓励多学科合作,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患者需求。
2.2 护理人员培训水平不一
目前我国护理人员在肝胆肿瘤领域的培训水平受地区、培训设施和方法等影响,存在差异,这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护理质量,也制约了该领域护理工作的进步和发展。肝胆肿瘤护理涉及到复杂的护理技能,如术前护理、术后并发症的护理、化疗护理等。需要护理人员具备精湛的临床技能和操作经验。然而,由于培训水平的不均衡,一些护理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技能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患者的安全和康复。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肝胆肿瘤护理的培训水平。首先,需要建立全面的培训体系,包括系统的课程、实践操作培训等。其次,鼓励护理人员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肝胆肿瘤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建议加强医疗机构之间的经验分享和合作,促使护理人员接触到丰富的临床经验,提升自身护理水平。
总体而言,我国肝胆肿瘤护理的培训水平需更加全面、系统,以确保护理人员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患者提供更高水平的护理服务。促使整个领域的护理水平得到提升,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
2.3 个体化护理实施不足
个体化护理作为一种关注患者独特需求和特征的护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在实际护理中,其推广和实施却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医疗体系的组织和资源分配,也涉及到医护人员的培训和意识转变。
首先,医疗体系的组织和资源分配是个体化护理推广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医疗机构中,资源分配仍然倾向于传统的集中式模式,难以满足个体化护理的需求。个体化护理需要更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但部分医疗机构可能因为经济压力或组织结构限制难以进行有效调整,个体化护理难以在广泛范围内得到贯彻。
其次,医护人员的培训和意识转变是个体化护理实施的另一瓶颈。传统的医疗模式通常强调标准化的护理流程,而个体化护理则要求医护人员具备更为灵活调整、专业的护理技能。然而,一些医护人员可能在培训中未能充分接触到个体化护理的理念和方法,导致在实践中难以主动运用。此外,推行个体化护理需要医护人员更强的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这也需要一定的培训和意识的转变。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从多个层面入手。首先,医疗机构需要优化资源分配,提高对个体化护理的投入,包括增加专业护理人员、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等。其次,培训课程应当更加强调个体化护理的理念和实践技能,确保医护人员具备开展个体化护理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此外,倡导医疗团队的协作文化,促使医护人员更好地协同工作,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全面的护理服务。
2.4 康复护理体系不健全
肿瘤康复是多学科合作、多模式康复理念,肿瘤康复团队应包括康复科医师、肿瘤科医师、心理科医师、营养科医师及社会活动家等[106],存在模式较为单一且康复服务管理缺失。
其次对于康复措施有效性的评定缺乏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研究,肝胆肿瘤康复质量的评定标准尚无法统一,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进行支持。另外最主要的是目前大多数临床护士对肝胆肿瘤的全周期康复意识偏弱,缺乏肝胆肿瘤康复全程管理的概念,而肿瘤康复应是连续的,并贯穿于肿瘤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全周期康复是未来肝胆肿瘤患者康复的全程管理方式,未来肝胆肿瘤患者的康复有望通过基于数字化医疗的全周期康复模式来进行干预,可贯穿肝胆肿瘤患者康复的各个阶段,而不仅仅局限在围术期康复。
医疗机构也应当加强对康复护理的认识,将其纳入全面治疗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需要增加康复专业人员的配置,提高其在肝胆肿瘤治疗中的参与度。同时,促进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建立跨学科团队,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康复护理的全面覆盖。
2.5 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不足
肝胆肿瘤的诊断和治疗过程往往伴随着患者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但是,尽管在医疗领域越来越重视患者的整体健康,肝胆肿瘤护理中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却相对不足。缺乏足够的心理支持可能会对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改善肝胆肿瘤护理中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不足的问题,医疗机构应该在护理团队中引入专业的心理医生,提供定期的心理支持服务。为患者提供信息和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疾病和治疗过程,有助于降低心理负担。同时,家庭成员和社会支持系统的纳入也是关键,可以通过建立患者支持团体、提供社会服务等方式来强化整体支持体系。
综上所述,肝胆肿瘤护理中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不足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通过增加心理专业人员的参与、提供全面的心理支持服务以及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可以有效改善肝胆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
2.6 护理研究国际合作程度有限
我国在肝胆肿瘤护理研究的国际合作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如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不足、国际学术交流机会有限、研究成果推广不及时等。
要提升我国肝胆肿瘤护理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国际间学术合作,鼓励科研机构与国际同行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攻克肝胆肿瘤护理领域的科研难题。建立国际数据库和研究网络,与国际研究团队合作,共同开展多中心研究,扩大研究样本量,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其次,建立国际研究平台,支持研究人员参与国际性学术交流,通过国际学术刊物、网络平台等渠道,广泛传播肝胆肿瘤护理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鼓励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提高肝胆肿瘤护理研究在国际护理学术界关注度和认可度。同时,建立完善的科研成果推广机制,促进肝胆肿瘤护理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应用于国际临床实践。
尽管我国肝胆肿瘤护理学科研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上述不足之处仍然存在。通过加强长期研究、提升护理人员培训水平、推动个体化护理实施、完善康复护理体系、关注患者心理健康、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努力,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国肝胆肿瘤护理的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全面、高效的护理服务。
【主编】
黄中英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沙丽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主编】
宋汉歌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仲冬梅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余静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杨 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福霞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勾玉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韩远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陶 丽 浙江省肿瘤医院
游雪梅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丽霞 四川省肿瘤医院
段仁茹 亳州市人民医院
郭中献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高 玲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何 叶 江西省肿瘤医院
林海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静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潘月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慈溪医院
王 汝 邢台市第一医院
余 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殷 琪 九江医学院附属医院
杨佳平 沧州市人民医院
左雪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 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ung H,Ferlay J,Siegel R L,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CA Cancer J Clin,2021,71(3):209-249.
[2] Cao W,Chen H D,Yu Y W,et al. Changing profiles of cancer burden worldwide and in China: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J].Chin Med J,2021,134(7):783-791.
[3] Zheng R S,Qu C F,Zhang S W,et al. Liver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temporal trends and projections to 2030[J]. Chin J Cancer Res,2018,30(6):571-579.
[4] YuS X,Wang H W,Hu T Y,et al. Disease burden of liver cancer attributable to specific etiologies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9: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J].Sci Prog,2021,104(2):368504211018081.
[5] Zou Z Y,Zhang Z F,Lu C,et al. Comparison of time trends in the incidence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J].Chin Med J,2022,135(17):2035-2042.
[6] Cao M M,Ding C,Xia C F,et al. Attributable deaths of liver cancer in China[J]. Chin J Cancer Res,2021,33(4):480-489.
[7] Ganesan P, Kulik L 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ew developments[J]. Clin Liver Dis, 2023, 27(1):85-102.
[8] Roth G, Villeret F, Decaens T, et al. Immunotherap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ow does underlying liver disease influence therapeutic strategy and outcomes?[J]. Liver Int, 2023, 43(3):546-557.
[9] Brandi G, Tavolari S, Biasco G. Genomic and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 identifies therapeutics targets f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J]. Gastroenterology, 2012, 143(4): e20-21; author reply e21.
[10] Banales J M, Marin J J G, Lamarca A, et al. Cholangiocarcinoma 2020: the next horizon in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J].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20, 17(9): 557-588.
[11] Hewitt D B, Brown Z J, Pawlik T M. Surgical management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Expert Review of Anticancer Therapy, 2022, 22(1): 27-38.
[12] Sohal D P S, Shrotriya S, Abazeed M, et al.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biliary tract cancer[J]. Critical Reviews in Oncology/Hematology, 2016, 107: 111-118.
[13]张正凤, 杨磊, 王大榛, 等. 局部进展期或晚期胆道恶性肿瘤治疗的现状及进展[J]. 中国肿瘤, 2022, 31(7): 569-577.
[14] Strom B L, Maislin G, West S L, et al. Serum CEA and CA 19-9: potential future diagnostic or screening tests for gallbladder canc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1990, 45(5): 821-824.
[15] Tsumura T, Doi K, Marusawa H. Precision Medicine of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Cancers: Focusing on Clinical Trial Outcomes[J]. Cancers, 2022, 14(15): 3674.
[16] Csoma S L, Bedekovics J, Veres G, et al.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Based Comprehensive Molecular Analysis of Biliary Tract Cancers Using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Cancers, 2022, 14(1): 233.
[17] Guo X, Shen W. Latest evidence on immunotherapy for cholangiocarcinoma[J]. Oncology Letters, 2020, 20(6): 1-1.
[18] Yaprak S. Ordin, Özgül Karayurt. Effects of a Support Group Intervention on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J].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Transplantation, 2016, 14(3): 329-337.
[19] 周海英, 张玉侠, 陈潇, 等. 肝癌患者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22, 57(2): 182-187.
[20] 史金凤, 王娜, 司文, 等. 基于2种模型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动脉栓塞化疗术后延迟性恶心呕吐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3, 39(21): 1628-1635.
[21] 周杉杉, 丁红梅, 徐雪萍, 等. 两种工具在原发性肝癌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延迟性化疗相关恶心呕吐风险评估中的比较[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2, 28(4): 452-457.
[22] 刘萍, 唐敏, 邹静. 基于症状管理理论的干预模式应用于肝细胞癌患者的效果[J].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 2022, 8(11): 142-144.
[23] 陈丽娜, 徐春艳, 安彬彬, 等. 基于症状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术后腹胀症状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2, 38(1): 61-66.
[24] 张建凤, 段鸿燕, 沈霞, 等. 原发性肝癌TACE治疗患者症状群及前哨症状的调查[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3, 29(28): 3884-3889.
[25] 郭燕, 贾守梅. 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疼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护士进修杂志, 2020, 35(4): 326-329.
[26] 卞丽芳, 高蓓蕾, 张晟, 等.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患者发生急性中重度腹痛的危险因素分析[J]. 中华护理杂志, 2020, 55(3): 416-421.
[27] 卢沛, 高春辉, 张璐, 等. 肝穿刺射频消融术后患者发生急性中重度腹痛的危险因素分析[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1, 19(37): 1480-1483.
[28] 杨慧杰, 翟慧敏, 李海兰, 等. 肝癌患者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疼痛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2, 38(24): 1885-1891.
[29] 李素婷, 李红杰, 王艳红, 等. 不同疼痛量表在肝癌患者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疼痛评估中的应用比较[J]. 护士进修杂志, 2021, 36(15): 1345-1348+1353.
[30] 行博荣, 李育玲, 王嵘, 等. 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对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患者术中焦虑与疼痛的影响[J]. 现代临床护理, 2023, 22(8): 32-37.
[31] 陈瑜, 黄道琼, 李海燕, 等. 肝癌栓塞术后疼痛患者择时给药时间点的改进及效果[J]. 中华护理杂志, 2019, 54(3): 393-395.
[32] 常艳丽, 王舒. 护士主导下认知和运动训练对中晚期肝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改善作用[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9, 35(11): 842-842.
[33] 李芳, 高建蕾, 李静, 等. 聚焦解决模式联合共情护理对肝癌术后患者癌因性疲乏及心理复原力的影响[J]. 齐鲁护理杂志, 2021, 27(8): 30-32.
[34] 柯卉, 陈俊华. 肝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焦虑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 2020, 20(8): 583-587.
[35] 郑琴, 王恺, 周颖, 等. 自尊和乐观对肝细胞肝癌病人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与抑郁症影响的中介作用[J]. 护理研究, 2021, 35(4): 602-607.
[36] 赵新华, 赵凌云, 韦珏伶, 等. 短期结构式心理教育对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为B/C期的肝癌患者抑郁情绪及免疫功能的影响[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9, 25(14): 1764-1764.
[37] 李琼霞, 张敏, 张学华, 等. 综合护理教育对肝癌患者术后抑郁、焦虑和生命质量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1, 37(11): 850-856.
[38] 王娜, 史金凤, 赵蓉, 等. 原发性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2, 38(18): 1400-1405.
[39] 柳书悦, 何凤英, 陈梅先, 等. 自我效能在肝癌术后患者恐惧疾病进展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效应[J]. 护理管理杂志, 2021, 21(2): 91-94.
[40] 付欢英, 金望迅, 徐英萍, 等. 肝癌腹腔镜根治术后患者癌症恐惧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34(27): 4680-4684.
[41] 伊静, 董建俐, 程洋, 等. 200例肝癌首次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患者心理痛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护理学报, 2020, 27(11): 61-65.
[42] 李小银, 卢海婷, 王玛丽, 等. 舒缓护理联合心情日记对晚期肝癌患者心理痛苦和负性情绪的影响[J]. 现代临床护理, 2023, 22(8): 42-47.
[43] 王红丽, 徐春艳, 张翠萍. 多学科协作模式延续护理在肝癌术后病人中的应用效果[J]. 护理研究, 2019, 33(7): 1202-1206.
[44] 王小平, 朱艳霞, 谢秋莉. Snyder希望理论结合院外移动平台在肝癌术后护理中的应用[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0, 26(15): 2050-2054.
[45] 汪海岚, 张晓红, 周丽娟. 纽曼系统护理模式联合微信平台干预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治疗病人中的应用[J]. 护理研究, 2020, 34(22): 4108-4110.
[46] 白黎, 王小平, 梁红霞. 医养结合-四元联动整合照护在晚期肝癌患者院外护理中的应用[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9, 25(22): 2870-2873.
[47] Song J xiang, Tu X huang, Wang B, et al. “Fast track” rehabilitation after gastric cancer resection: experience with 80 consecutive cases[J]. BMC gastroenterology, 2014, 14: 147.
[48] Zhao J H, Sun J X, Gao P, et al. Fast-track surgery versus traditional perioperative care in laparoscopic colorectal cancer surgery: a meta-analysis[J]. BMC cancer, 2014, 14: 607.
[49]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中国加速康复外科临床实践指南(2021)(一)[J]. 中华麻醉学杂志, 2021, 41(9): 1028-1034.
[50] 王红丽, 陈玲, 徐春艳, 等. 加速康复外科肝癌病人围术期护理方案的构建及应用效果[J]. 护理研究, 2019, 33(23): 4060-4064.
[51] Lim D S. Prehabilitation--Is It Worth Our While?[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2015, 94(8): e74.
[52] 冯碧, 许瑞华. 三联预康复策略在肝癌腹腔镜肝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J]. 现代肿瘤医学, 2019, 27(10): 1761-1765.
[53] 王静, 唐小丽, 邹静, 等.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下肝癌患者围术期全程胃肠道管理[J]. 护理学杂志, 2019, 34(10): 1-4.
[54] 周毅峰, 杨继平, 袁浩, 等. 肝癌加速康复外科术中保温技术的循证实践[J]. 护理学杂志, 2019, 34(10): 12-16.
[55] 丁文斌, 倪创业, 壮麟, 等. 术后不放置腹腔引流管在肝癌切除手术患者加速康复外科中的应用[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6(3): 365-367, 384.
[56] 王艳晖, 岳仙, 郑瑞双, 等.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下出院准备管理方案在肝癌术后患者中的应用[J]. 护士进修杂志, 2022, 37(24): 2267-2271.
[57] 王霄霄, 方秀新, 郑春辉, 等. 基于零缺陷管理理论构建肝胆外科加速康复评价指标体系[J]. 护理学杂志, 2019, 34(10): 8-11.
[58]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 2017(2): 44-47.
[59] Ellershaw J E, Peat S J, Boys L C.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hospital palliative care team[J]. Palliative Medicine, 1995, 9(2): 145-152.
[60] Osse B H P, Vernooij M J F J, Schadé E, et al. Towards a new clinical tool for needs assessment in the palliative care of cancer patients: the PNPC instrument[J].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2004, 28(4): 329-341.
[61] Buzgova R, Kozakova R, Sikorova L, et 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patient needs assessment in palliative care (PNAP) instrument[J]. Palliative & Supportive Care, 2016, 14(2): 129-137.
[62] 吴洪寒, 陈湘玉, 殷小莉. 癌症患者安宁疗护需求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护理学杂志, 2020, 35(7): 5-8.
[63] Hearn J, Higginson I J.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core outcome measure for palliative care: the palliative care outcome scale. Palliative Care Core Audit Project Advisory Group[J]. Quality in health care: QHC, 1999, 8(4): 219-227.
[64] 俞人悦, 张露芳, 黄道琼, 等. 晚期肝癌介入术后患者安宁疗护需求的质性研究[J]. 介入放射学杂志, 2023, 32(2): 185-187.
[65] 崔雪, 王红丽, 徐春艳. 晚期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需求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9, 42(9): 1211-1215.
[66] 沙小琴, 杨文英, 李星, 等. 基于循证理念的临终关怀干预在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 癌症进展, 2019, 17(15): 1847-1851.
[67] 周晓丰, 魏攀. 基于生命意义的死亡教育在原发性肝癌病人晚期护理中的应用价值[J]. 护理研究, 2019, 33(5): 893-896.
[68] Rumgay H, Arnold M, Ferlay J, et al. Global burden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in 2020 and predictions to 2040[J].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2, 77(6): 1598-1606.
[69] Khuntee W, Hanprasitkam K, Sumdaengrit B.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postembolization syndrome in Thai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quasi-experimental crossover study[J]. Belitung Nursing Journal, 2022, 8(5): 396-404.
[70]Kim M S, Kang M, Park J, et al. Nurses’comfort care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patients based on their perceptions around postembolization syndrome and symptom interference[J]. Nursing Open, 2022, 10(5): 2877-2885.
[71] Hansen L, Dieckmann N F, Kolbeck K J, et al. Symptom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oward the end of life[J]. Oncology Nursing Forum, 2017, 44(6): 665-673.
[72] Ni C yan, Hou G jun, Tang Y yuan, et al.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early standardized ambula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after hepatectomy[J]. Frontiers in Surgery, 2022, 9.
[73] Kelly D, Fernández-Ortega P, Arjona E T, et al. The role of nurs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renal and hepatic cancer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European Oncology Nursing Society, 2021, 55: 102043.
[74] Devictor J, Leclercq A, Hazo J B, et al. Nurse coordinator roles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French national survey[J].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 2021, 45(3): 101650.
[75] Ow T W, Ralton L, Tse E. Saving costs through a coordinated care model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ncer[J]. 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 2017, 47(9): 1005-1011.
[76] Bell J F, Whitney R L, Reed S C,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hospital readmissions among patients with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J]. Oncology Nursing Forum, 2017, 44(2): 176-191.
[77] Liu L, Zhang M, Zhang X, et al. Effects of enhance recovery after surgery nursing program on the surgical site wound infec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hepatectom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J]. International Wound Journal, n/a(n/a).
[78] Feng J, Li K, Xu R,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compliance with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protocols and postoperative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undergoing hepatic resection[J].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 2022, 148(11): 3047.
[79] St-Amour P, St-Amour P, Joliat G R, et al. Impact of ERAS compliance on the delay between surgery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malignancies[J]. Langenbeck’s Archives of Surgery, 2020, 405(7): 959-966.
[80] Romo R D, Allison T A, Smith A K, et al. Sense of Control in End-of-Life Decision-Mak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017, 65(3): e70-e75.
[81] Avila V, Paik J M, de Avila L, et al. Hospice care utilisation among elderly patients who died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he United States[J]. JHEP reports: innovation in hepatology, 2021, 3(2): 100236.
[82] Fukui N, Golabi P, Otgonsuren M, et al. Hospice care in Medicare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the impact on resource utilisation and mortality[J]. 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2018, 47(5): 680-688.
[83] Hansen L. Living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ear the End of Life: Family Caregivers’Perspectives[J]. Number 5 / September 2017, 2017, 44(5): 562-570.
[84] Pettifer A, Froggatt K, Hughes S. The experiences of family members witnessing the diminishing drinking of a dying relative: An adapted meta-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J]. Palliative Medicine, 2019, 33(9): 1146-1157.
[85] Pan H, Su J, Zhao T, et al. Effect of hospice care on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 of core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iver cancer[J].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Research, 2021, 13(5): 5322-5328.
[86]李建华. 综合护理改善52例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J]. 中国中医急症, 2012, 21 (10): 1713-1714.
[86]李春艳.分析多学科联合协作在肝癌手术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J].中国医药指南, 2023, 21 (30): 166-168.
[88]吴娜,柴真真.围手术期多学科团队护理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疼痛和社会支持的影响[J].肿瘤基础与临床,2023,36(5):446-448.
[89]华桂荣,钟翠萍,彭爱梅.多学科协作诊治模式在TIPS治疗原发性肝癌伴门静脉高压病人护理中的应用 [J]. 全科护理, 2019, 17 (16): 1998-2000.
[90]袁卉,朱硕,王海红,等.量化评估策略指导下个体化护理干预对肝癌术后患者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23,29(8):29-32.
[91]张磊,朱晓瑜,吴燕.基于快速康复理念的个体化干预在肝癌术后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J].当代护士·专科版,2023,30(1):91-94.
[92]范文芳.个体化护理干预对肝门胆管癌手术患者术后恢复、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影响[J].慢性病学杂志,2019,(9):1403-1405.
[93]蒋慧,曹影.基于行为改变理论的健康教育模式在肝癌患者中的应用[J].当代护士·综合版,2023,30(7):148-151.
[94]孙柳君,张琼,鲍映雪.健康教育联合心理干预对腔镜下胆管癌根治术患者的护理影响[J].浙江临床医学,2019,21(5):694-695.
[95]李艳敏,王翠田,李洁,等.聚焦解决模式的健康教育在腹腔镜肝血管瘤切除术患者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23,29(12):133-136.
[96]马丽,张爽,赵薇,等.基于互联网信息化健康教育在肝癌术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J].护理实践与研究,2023,20(9):1360-1363.
[97]周美灵,吕传阁,王伟阁. 晚期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预见性护理[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23, 20 (18): 2789-2794.
[98]刘晓芹,欧阳玉莲. 亲情—责任交互式护理干预在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J]. 当代护士(上旬刊), 2023, 30 (09): 77-81.
[99]王淑芳,武素珍. 系统化管理干预应用于急诊肝癌合并消化道出血患者护理质量及预防并发症效果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3, 26 (S1): 44-46.
[100]杨捷. 快速康复联合个性护理对肝癌患者术后WHOQOL-100评分的影响[J]. 当代护士(中旬刊), 2020, 27 (09): 74-76.
[101]侯晓敏,米娜,李洪艳. 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相关并发症的个性化护理[J]. 当代护士(下旬刊), 2020, 27 (01): 44-46.
[102]张晶晶,庞文燕,王云等. 基于集束化策略的护理干预在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及其对疼痛及PSQI评分的影响[J]. 现代医学, 2023, 51 (07): 991-996.
[103]王红,范伟,李艺等. 心理护理结合循证护理对肝癌患者疼痛、疲乏及负面情绪的影响 [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31 (09): 1284-1287.
[104]高慧. 肝癌患者应用快速康复护理对术后并发症与康复效果的影响[J]. 当代护士(上旬刊), 2020, 27 (05): 73-74.
[105]侯晓敏,米娜,李洪艳. 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相关并发症的个性化护理[J]. 当代护士(下旬刊), 2020, 27 (01): 44-46.
[106]余陈贵,殷保兵.肝胆肿瘤围术期康复的进展[J].中国医刊,2022,57(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