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立即下载App贝家讲坛 | 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风云变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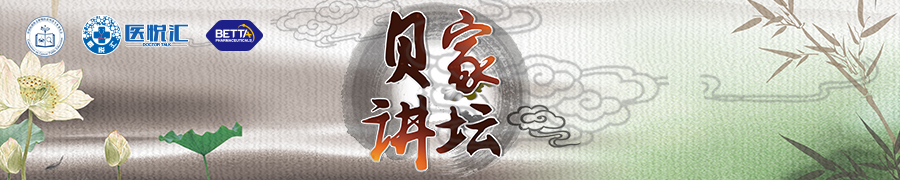
众所周知,肺癌是严重危害我国国民健康的恶性肿瘤,经过众多医务工作者不断的钻研和探索,新药物新技术相继问世,治疗方案不断的改良,相比以往肺癌患者也获得了更好的治疗,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对于肺癌的整体治疗和研究依然还有很多的未解之题。回顾过往、总结当下、思考未来是医学发展和进步的前提,追寻更好、更优、更有温度的治疗模式,是每一个医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贝家讲坛》关注肺癌前沿进展,关注临床诊疗实践,每期邀请领域大咖、青年医师,聚焦热点话题,一起忆往昔、看今朝、思未来,共同探讨肺癌全程管理的攻守之道!
本期嘉宾

领域大咖
石远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
主持人
刘雨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青年医师
梁乃新 北京协和医院
徐 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梁文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正文↓↓↓
欢迎收看《贝家讲坛》,我是主持人刘雨桃,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本期《贝家讲坛》特邀国内著名肺癌诊疗专家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石远凯教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支修益教授,聚焦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风云变幻,让我们跟随他们一起忆往昔、看今朝、思未来,探讨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攻守之道。
忆往昔-青年医师说
对比刚工作时,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经历了哪些改变?
梁文华教授:我刚进入临床时,只有II/III期的病肺癌患者需要给予辅助化疗,Ⅰ期患者不需要,而ⅠB期则有一定的争议。2013年,我们做过一个术后的生存预测模型,那时没有条件做基因分型,如今肺癌的个体化治疗理念已经非常普遍,也意识到基因分型的重要,其与患者术后复发者转移的风险以及模式都是有关系的。
梁乃新教授:肺癌患者的治疗近几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工作最初时,外科大夫并不太关心后期的治疗,只管做手术。近5年开始,精准医学的理念逐步走到了肺癌的全程管理中,现在胸外科医生有很多已经开始基于手术标本的精准检测结果来为病人挑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至于这样的治疗方案能否提高5年生存率或更长的生存期上还是拭目以待的。
忆往昔-领域大咖说
刘雨桃教授:看了这几段视频,相信可能也勾起了两位教授对自己当年参加工作时候的一些回忆,所以也想请两位教授给我们谈一谈,在您当初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肿瘤患者的一个生存的情况,以及经过了这些年肿瘤医学的一些发展之后,您觉得现在我们尤其是肺癌的这些患者,他们在生存上以及生活质量上都有哪些改善?
支修益教授:我刚进入临床开始接触肿瘤病人还是1980年。那时在朝阳医院临床实习,无论是结直肠癌、乳腺癌还是肺癌患者,术后复发和转移都非常常见,术后5年生存率很低。那时候术后辅助治疗还没有规范指南可以遵循,也没有参考过美国NCCN指南。那时是一个真正的“谈癌色变”的年代。这种恐惧不仅仅来源于“患癌”这两个字,更令患者恐惧的是特别大的手术创伤以及化疗毒副作用给患者带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信心的一种打击。
1983年,我到了北京市结核病肺部肿瘤研究所胸外科工作。那时大家普遍认为肺癌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就能治愈,无论是ⅡA期、IIB期、ⅢA期,甚至ⅢB期同样会做手术切除,因为当时术后近期效果很好,没有想过跟肿瘤内科合作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术后辅助化疗也都是我们胸外科大夫顺带着做。想当年,我每星期都会去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出胸部肿瘤门诊和参加肺癌MDT查房,后来借鉴学习他们医院创建了胸外科肺癌化疗病房,就是现在的肿瘤内科前身,一想至今已经30多年了。而且结研所胸外科在前30年更多是在治疗结核病。
石远凯教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结核,得肺癌的人没现在这么多。
支修益教授:对,术式没有肺癌外科手术复杂,肺癌外科手术除了肺部病灶切除,还需要进行清扫纵隔淋巴结,甚至有些还要气管支气管重建。那时我就开始在结核病医院科主任的安排下,在医科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学习,并跟着黄国俊教授、张大为教授一起出门诊,一方面跟着胸外科前辈接诊胸部肿瘤患者,一方面跟着老教授们学习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模式。当时在医科院肿瘤医院学习,有点像现在出国学习,那时医科院肿瘤医院门诊有一个独立的胸部肿瘤诊区,很早就开始了肺癌 MDT的诊疗模式,每周三还有肺癌MDT讨论,在这样的机缘下,加深了我对肿瘤内科的认识,并把MDT的理念带回科里。
石远凯教授:那时候徐嘉彰大夫每个礼拜到我们医院参加我们内科的大查房。
支修益教授:是的,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医科院肿瘤医院每周一上午出门诊,当时肿瘤医院肺癌的MDT病例讨论就给了我启发——肺癌治疗不能单靠一把刀,术后的辅助治疗至关重要,只是那时候我们结核病医院内科全是结核内科医生,没有肿瘤内科,所以肺癌术后的辅助治疗都是由我们胸外科医生自已来做的。所以,现在来看,我是属于比较早的开展肺癌术后辅助治疗、术前新辅助治疗的胸外科医生。
石远凯教授:支教授和刚才几位年轻大夫说的话也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知道历史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我1984年毕业之后,做了4年的外科大夫,还记得当时来北京参加肿瘤内科的研究生考试,我的同学跟我说,(肿瘤内科)这个专业你不能念,我说怎么不能念?他说你看中国有几个地方有肿瘤内科的专业科室,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都困难。但是你看现在什么样?这几十年肿瘤内科的发展真是不可同日而语。20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综合医院和肿瘤专科医院有肿瘤内科独立科室建制的非常少。那时候肿瘤的治疗就靠一把刀,外科大夫顺带打化疗。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做完手术之后要给病人打化疗。打多少?大夫觉得应该打多少就打多少,根本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指南、规范说要怎么做,都是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做治疗,那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年代。1985年我到北京开会,正好跟孙燕院士一起参加中日肿瘤学术交流会,我给孙燕院士做日语翻译,做完翻译之后,我就对肿瘤内科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孙燕院士跟我说,外科的力量比内科强很多,但是从肿瘤的本质而言,他是一个全身病,全身病肯定要全身治疗,全身治疗怎么治?就是药物治疗。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上升到基因治疗、免疫治疗,但是就是这朴素的对肿瘤本质(肿瘤是一个全身性疾病)的认识,就坚定了我的决心,认为肿瘤内科治疗一定是大有可为的,后来我就开始改行了,可以说这次会议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非常的幸运。
支修益教授:您从事外科,也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
石远凯教授:但是内科这几十年的发展是特别迅猛的,对此真是深有感触。
支修益教授:我也印象很深,那时候医科院肿瘤医院床位很少,在日坛公园附近,后来才搬到了现在的左安门位置。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前身还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肿瘤研究所,几十张床,如今已经发展成我国知名的肿瘤专科医院。
石远凯教授:是呀,那时候肿瘤的治疗是以外科为主,内科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如今外科一把刀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了,包括外科大夫都认为,肿瘤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刚才支教授讲,我们医科院肿瘤医院前身还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时,我们的前辈们就最早建立了淋巴瘤的综合治疗组。此外,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孙燕院士领着我们做肺癌的多中心协作研究,搞京津冀合作,北京、天津、河北一起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支修益教授:是呀,现如今大多数医院的胸外科医生也开始给肺癌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和分子分型,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念深入临床,我还在2003年初创建成立了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
石远凯教授:我记得首医大肺癌诊疗中心去年还举行了成立16周年的庆祝大会。
支修益教授:对,当时很多医科大学或胸科医院还不具备成立多学科参与的肺癌诊疗中心条件的。现在也已经有了MDT的理念——胸外科跟所在医院的肿瘤科、呼吸科进行多学科合作,很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都成立了有胸外科、肿瘤科和放疗科共同参与的肺癌诊疗中心,像中日友好医院还有中西结合肿瘤科。
石远凯教授:学科的发展也需要适应社会的需求。老百姓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肿瘤实际上是一个老年性疾病,随着预期寿命不断增加,发生肿瘤是大概率事件,病人比原来多多了,所以有巨大的社会需求。那么怎么样能让效果越来越好?能给病人创造更多的治疗的机会和治疗的方法。这写都从客观上促进了我们更加努力的去做全面的思考,做这方面的研究。
刘雨桃教授:谢谢两位教授帮我们一起回顾了近半个世纪肿瘤发展的历程,两位教授更是我国肿瘤发展事业的见证人,从刚才两位教授的回忆中,我深刻感受到,当年的肿瘤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肿瘤的治疗缺乏有效的手段,患者经历了很多的不良反应,生存期也非常有限。甚至在术后辅助治疗中,很多患者即便是经历了不良反应,依然只得到很短的生存期。如今看到肿瘤医学的发展,尤其是肿瘤内科治疗发展到今天,肿瘤治疗的目标已经转化为将肿瘤变成慢性病,我们也更加希望的是让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忆往昔-青年医师说
在延长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和降低复发转移风险方面,术后辅助治疗做出了哪些贡献?
徐嵩教授: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Meta分析告诉我们,术后辅助化疗可以提高患者术后的5年生存率,能够提高5%这么一个绝对值。当然还需要探索更加高效低毒的治疗模式。
梁文华教授:术后辅助治疗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术后辅助治疗采用全身治疗的方法,把一些还探测不到的微残留灶或微转移灶杀灭,能够实现一个根治的目的。假如不能杀灭,也能延缓复发的时间。
领域大咖说
刘雨桃教授:今天,肿瘤治疗的目标已经转化为将肿瘤变成慢性病,想问问两位教授,对于现在肿瘤医学发展的目标上,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目标的转变?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和大家分享?
支修益教授:其实这个问题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国家的癌症科技攻关行动计划也已经列出来了。首先,早期肺癌的诊疗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上个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用胸部CT代替了胸透和胸片进行肺癌早期筛查。随着肺癌早诊科普宣传、肺癌筛查项目的开展,更多的早期肺癌走进了我们临床。特别是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使得胸部CT的检查全面铺开,也让很多肺结节和早期肺癌走进我们胸外科的视野。其次,肺癌外科手术逐渐微创化,使更多的早期肺癌获得了更长的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此外,患者的病理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年前肺癌病理类型以中心型肺鳞癌为主,如今则以周围型肺腺癌更多见,肺癌药物治疗的选择也随之改变。总体而言,我认为 胸部CT的普及和应用有助于更多早期肺癌的发现,有利于改变肺癌患者整体的5年生存率。最后,随着国内更多的民族原研抗肺癌新药出炉,临床单兵作战模式已经转变为多学科MDT诊疗模式,也使更多的局部中晚期肺癌患者从经济和疗效上双重获益。
石远凯教授:现在,外科治疗主要以微创为主,放射治疗也转变为精准放疗。内科治疗在含铂方案化疗之后,抗血管生成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逐步进入临床,可以说,每隔10年左右就会出现巨大的突破。比如靶向治疗,随着基因检测技术、分子分型技术的发展,肺癌尤其是肺腺癌也有了更细致的划分,EGFR突变、ALK突变等多种类型。以往N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最好的数据是12个月左右,但有了一代的EGFR-TKI、ALK-TKI之后,治疗效果发生了质的改变。现在随着三代EGFR-TKI,抗血管靶向治疗药物以及其他一些新型的药物的出现,我想更多有效的药物还会不断地被发现。
支修益教授:在这里我也希望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无论是我们医务人员,还是我们的社会朋友,都要远离烟草。
刘雨桃教授:好的,谢谢。从两位教授的刚才讨论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现在肿瘤患者之所以能够活的更长,活的更好,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筛查手段的改变,让我们不用像七八十年代那样,一经诊断80%以上都是晚期。更早的发现早期肺癌,开展多学科治疗,患者的生存期必然能得到了更多的改善。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像石院长所说的,在近20年来,治疗肿瘤的药物发展突飞猛进,我们比原来有了更多有效的治疗药物。诊断和分型都有了更好的技术,从基本的化疗到现在更精准的靶向治疗,还有针对微环境的抗血管治疗和免疫治疗,都给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更好的生存获益。当然,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刚才支教授所说的,无论治疗手段多么先进,给患者带来多大的获益,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远离癌症的危险因素,从根本上降低肿瘤的发病率。
经过20多年的探索,肺癌诊疗医生们在临床研究和实践中逐渐达成了新的共识,形成了新的诊疗方案,给众多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那么我们的临床医生是如何一步步达到今天的成就的呢?随着靶向治疗的诞生,肺癌术后辅助治疗又经历了哪些风云变幻?未来需要我们去探索的方向有哪些?请大家继续关注《贝家讲坛》,我们将在下期中为您揭秘。